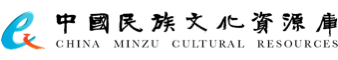
[提要]两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互动往来激增,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观念前后经历了多重变化。本文主要从宋廷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朝贡关系变化的角度,具象地把握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变化趋势,从而梳理辨析出两宋针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存在着有明显差异的三个时期。同时,宋代较之前代,打破了单一的羁縻治理方式,开始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与政治需求,灵活调整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方式,对政权的发展运作更具有现实意义。
两宋时期,中央政权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互动往来激增,双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也较前代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专门针对处理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民族治理观念应运而生。学界已有诸多针对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政策的论述,而其中也或多或少涉及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观念。①但以往学者却较少用变化的视角观察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前后变动。本文旨在从宋廷与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关系变化的角度,来窥探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变化的几个变迁时期,进一步阐释其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唐末,诸酋分据其地,自为刺史。宋兴,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间有桀黠贪利或疆吏失于抚御,往往聚而为寇,抄掠边户。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1](P.14209)《宋史·蛮夷传》较为笼统地概述了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大致,但宋代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观念其实经历了前后变动,可依其性质和特点,划分为北宋前期、北宋中后期以及南宋时期三个时段。
一、北宋前期
赵匡胤代周建宋后,继续实行后周世宗“先南后北”的统一政策,依次攻灭荆南、后蜀等政权,使得宋廷的统治触角第一次触及西南地区。但受制于统一战争的持续推进,宋廷并未对西南复杂的少数民族区域进行过多的政治深入,就连沿边的州军长官,也多选择“蛮夷”担任。在这一时期,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态度,更多是呈现荒置不问的状态,其目的正是在于绥靖边境。如任命辰州傜人秦再雄为辰州刺史,统御南北江溪峒诸部族。再由秦再雄派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来之意”,溪峒诸部族“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 [1](P.14180)在攻灭后蜀之后,即停止了近一步的外拓。尤其是在黎州沿边,“鉴唐之祸,乃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宼不能,欲臣不得。”[2](P.1978) 泸州知州钱文敏在赴任前,太祖也告诫称:“泸州近蛮,尤宜抚绥。” [3](P.346) 在此观念主导下,宋廷针对西南少数民族请求纳贡的意愿,全部接纳之,从而开启了宋朝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朝贡往来。
开宝九年(976),宋太宗嗣位,继续进行着太祖未尽的统一大业。在平定南唐,收复北汉之后,宋廷对外重心又转向北方的契丹。因此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也多秉承太祖,以绥靖羁縻为主,但在具体治理方式上有所调整。如派遣兵部侍郎许仲宣亲赴大渡河,晓谕寇扰边境的“西南夷”;[3](P.465)对数寇边境的抚水蛮,诏书招安,补其首领官职;太平兴国二年(977)又以李崇矩为邕、贵、浔、宾、横、钦六州都巡检使,“抵其洞穴抚慰,以己财遗其酋长,众皆怀附。”[1](P.9266) 这改变了太祖朝任命“蛮夷”担任沿边州军长官,间接向西南少数民族首领传达朝廷谕旨的治理方式,而是指派朝廷官员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直接宣告朝廷旨意,或身体力行,规劝西南少数民族降伏。这一直接性的沟通,更能彰显宋廷的诚意,促使一些荒服不至的西南少数民族“皆率服”,并纷纷赴阙来朝。
转至真宗时期,随着澶渊之盟的签订,宋廷正式结束了与契丹的战争。宋朝创制以来剑拔弩张的战争氛围也就此消散,宋廷统治重心也逐渐由外及内。在此背景下,统治者对西南地区的关注也与日俱增。真宗称:“比来备边,专意西北。至于远方殊俗,要不可忽,如川、广、荆湖,常训齐军伍,以为备边也。”[3](P.1213)其所言川、广、荆湖的备边,正是指向西南少数民族。因为在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民族矛盾格外突出。大量汉民在稳定的政局下,纷纷开拓荒土,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荆湖、两广、以及川峽地区的“蛮乱”始终不息,其中以大中祥符元年(1008)一直持续到大中祥符三年的“泸蛮之叛”,以及大中祥符六年淯井监作乱事件影响最大。[3](P.1838-1839)这些冲突都对西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而宋廷的平叛战役又受山川地形的影响十分不顺,因此宋廷开始调整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方式,逐渐以朝贡为诱,降伏“蛮夷”,绥靖边境。大中祥符五年,夔州转运使就建议“溪峒蛮人结集为乱,俟发兵讨捕,则归先所掠汉口,及五十人者,承例特署职名,许令入贡。” [3](P.1793)即以归还汉人的数量为准绳,对自愿归还一定人口的西南少数民族开放朝贡之便。可见,从过去被动接纳朝贡,到主动利用朝贡,真宗朝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方式较前朝有所进步。而真宗朝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次数增多的另一个原因,正是真宗意图构建万国来朝的正统地位,以雪“澶渊之耻”。究其性质,当与封禅、祥符之法相埒。在真宗封禅的过程中,就有西南少数民族的参与。这从大中祥符元年,邛部川蛮与西南溪峒诸蛮随驾前往泰山封禅的史实中得以体现。[3](P.1563;P.1567)
诚然,真宗朝西南少数民族朝贡的种落数目与朝贡频率增多的背后,虽然隐藏了真宗不同前朝的政治期许,但总体上,宋廷在这一时期还是延续了对西南少数民族绥靖羁縻的统治政策。如真宗曾言:“朕常戒边臣无得侵扰外夷,若自相仇杀,但用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必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此尔。”[3](P.1641)当真宗满足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向通汉加封请求受到大臣们反对时,回应称:“檄外蛮夷,能慕风化,宜且从所请,向去制置可也。”[4](P.9881)而在向通汉内附请求定租税时,真宗又以“荒服不征,弗之许”。[1](P.14174)由上述事例可见,真宗在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朝贡往来欢迎的同时,对西南少数民族内部事物干预甚少,并始终谨守“夷夏之防”,对西南少数民族表现出即利用又防范的复杂心态。
仁宗朝继续秉持着前朝以来对西南少数民族绥靖羁縻的治理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西南少数民族一系列的朝贡制度。首先是对西南各少数民族朝贡时间的限制。如规定夔州路溪峒蛮人三年一贡[3](P.2420),邛部川蛮五年一贡[5](P.61)。此外,例如西南少数民族的“非时到阙”、护送流程也都在这一时期设计规范。仁宗朝就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制度的规定,不仅是出于规范礼节制度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对真宗朝过度招诱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情况的限制,如一些规模较小的西南少数民族就被排斥在朝贡体系之外,而道途遥远的部落则延长了他们朝贡的时限。与此同时,仁宗还继续将朝贡关系作为羁縻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并予以拓展。庆历四年(1044),宋廷就因罪禁止羁縻忠顺州刺史彭师宝贡奉,迟至皇祐二年(1050)才予恢复。又至和二年(1055),羁縻下溪州都誓主彭仕义叛乱之际,“朝廷姑欲无事,间遣吏谕旨,许以改过自归,裁损五七州贡奉岁赐”。[1](P.14178-14179)可见,这一时期朝贡资格的取缔,已逐渐成为宋廷惩罚触罪西南少数民族部落的主要手段。
与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制度逐渐规范史实相对应的是,宋廷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羁縻态度也发生了细微的转变。在宝元元年(1038)安化蛮叛乱之际,苏绅指出蛮夷骚动是因为“往者守将失计,而国家姑息之太过也”,他建议“秋冬之交,风气已息,进军据其出路……伺得便利,即图深入,可以倾荡巢穴,杜绝蹊径……不越一年,逆贼必就殄灭”,其提议受到了仁宗的赞赏。[3](P.2883-2285)又如庆历四年,广西转运使杜杞在讨平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区希范叛乱后,大杀“降蛮”五百余人。侍御史梅挚以其失朝廷“推信远人之意”,要求治罪杜杞。但仁宗却置之不理,依旧封赏杜杞等平叛官员。[3](P.3778)从上述两个事例可见,仁宗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态度已不像前朝那样,已逐渐转向了强硬,这也为之后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二、北宋中后期
北宋中期开始,朝廷中变法的呼声渐起,到神宗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执政,宋廷的内外政策都出现了巨大的转向。相应地,宋廷也改变了北宋前期为讲求边境安稳,过度羁縻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观念:
忠、万间夷人,祥符中尝寇掠,边臣苟务怀来,使人招其酋长,禄之以劵粟。自后有效而为之者,不得已,又以劵招之。其间纷争者至有自陈,若某人才杀掠若干人遂得一劵,我凡杀兵民数倍之多,岂得亦以一劵见给?互相计校,为寇甚者则受多劵。熙宁中会之,前后凡给四百余劵,子孙相承,世世不绝。因其为盗,悉诛锄之,罢其旧劵,一切不与。自是夷人畏威,不复犯塞。[6](P.78-80)
可见熙宁之前,在绥靖政策的主导下,边臣对西南少数民族过于注重怀抚,但在熙宁之后,宋廷的治理观念逐渐转向强硬。
首先,这一时期宋廷的政治力量开始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腹地,并将部分区域开拓吞并。熙宁七年(1074),荆湖南北路官员上报南北江溪洞蛮互相攻掠,下溪州都誓主彭师晏又懦弱无法服众,请求内附。朝廷立即派出章惇等官吏对南北江溪峒地区进行经制。收复了邵州与潭州交界的梅山地区,开置新化县;又降伏下溪州都誓主彭师晏,五溪皆平;紧接着开拓了南江地区,建立沅州。[3](P.5897;P.9986;P.6070)至熙宁九年,诚徽州三州一镇也被宋廷收归王土,建为靖州,“拓境数百里……南方兵祸自此始也”。[7](P.1530)在这次开拓的过程中,已完全没有宋初“怀服远夷”的绥靖之情。据《宋史·张颉传》记载,“南江杀戮过甚,无辜者十八九,浮尸蔽江,民不食鱼者数月”,[1](P.10669)可见宋廷此时对西南地区的开拓充满着血腥与残酷。
其次,宋廷提高朝贡门槛,进一步限制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次数。如正式规定了西南五姓蕃五年一贡的朝贡时限:“西南蕃五姓蛮听五年一入贡,不愿至京,听就邕、宜州输贡物,给恩赏馆券,回赐钱物等遣之。” [3](P.6451)诸如安化蛮等部分西南少数民族,则被要求不再赴阙朝贡,“令纳方物于宜州思立寨,而亲赴州领赐。”[8](P.121)
此外,自宋初开展的西南少数民族赴阙朝贡制度到了神宗之时,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的诟病。熙宁八年,广西经略司称西南五姓蕃每次赴阙朝贡,所赐“往来馆券供给,并到阙见辞赐钱、绢、衫带,为钱二万四千余缗,而他费不在此”[3](P.6451),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接待所耗可见一斑。而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沿路保障的关怀备至,也使西南少数民族贡使傲慢异常,甚至“与方伯抗礼”,[1](P.10706)从而导致地方上关于转变西南少数民族朝贡方式的呼声高涨。熙宁六年四月,西南龙蕃、罗蕃、方蕃、石蕃等八百多人入贡。宋廷“以道路辽远,往复甚勤如愿于缘边纳所贡物,即以回赐及朝见所赐缘路驿劵给之。”[3](P.5931)宋廷要求西南五姓蕃不再赴阙朝贡,在缘边交纳贡物即可,并在熙宁八年(1075)确定了邕州、宜州两个输贡之地。“后令纳方物于宜州思立寨,而亲赴州领赐。”[8](P.121)思立寨位于宜州以西七十五里之地,与安化州接壤,属于省地与蛮地交界地区。宋廷将输贡之地逐渐迁移至边界,一方面是方便“西南五姓蕃”运输贡物,另一方面更是基于宋廷对“西南五姓蕃”始终存有防范之心。
宋廷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态度转向强硬,朝贡要求逐渐严苛,这也与宋廷在神宗朝对外政策的转变密切相关。在北宋前期,宋廷的对外重心在北方,并始终处于防守之势。因此,针对西南地区,一直秉承“羁縻蛮夷,以其为边境藩篱”的政策方针。但自从神宗朝提出了“汉唐旧疆”的拓边计划后,使得西南少数民族“藩篱”的意义大为降低。在熙宁九年宋朝对交趾战争爆发之前,宋廷先后调派萧注、沈起为桂州知州,为进攻交趾做好了前期准备[1](P.10723)(P.10733) 至此,原本宋廷极力安抚,并希冀其成为隔绝西南边境之患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此时已沦为宋廷的拓边计划的绊脚石。王安石就曾谏言:“恐南师既行,彼(诚徽州杨氏部族)见中国无如我何,因交趾未服间,连结抚水,更为湘潭之患”,并建议神宗乘大军南下攻取交趾之际,一并铲除。[3](P.6740)而邕、钦二州溪峒及外界山獠,也“深虑一旦交贼荡灭,朝廷列其土为郡县,美利悉归公上。以势异患同之故,及交相党与,或阴持两端,或未决效顺”。[3](P.6767)受此影响,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态度逐渐转向强硬,不再过分强调羁縻。
哲宗一朝的统治政策前后有过反复,而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态度也有所变更。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羁縻诚徽州的废存问题。羁縻诚徽州自元丰时期收复后,原羁縻诚州改为正州,依旧行以诚州之名,而羁縻徽州则被改置为莳竹县。元祐二年(1087),宋廷改诚州为渠阳军,三年又废军为寨,并认为熙、丰之际,深入蛮界,致多疑惧,有违朝廷“疆理四海,务在柔远”的方针。[3](P.10075-10076)并一度准备恢复诚州,补授杨光潜之子杨昌达为刺史,重新在荆湖地区施行“以夷制夷”的政策。②但至绍圣之时,诚徽州处置问题上的首倡者唐义问,就因“坐弃渠阳寨,责受舒州团练副使”。[1](P.341)而就对待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关系而言,哲宗一朝却继续延续了神宗朝的收缩政策,始终未有太大的变动。元祐元年正月,南丹州莫世忍遣人进奉,哲宗诏准,但却再次重申不得赴阙。[3](P.8732)又元祐六年,施州、黔州蛮人入贡,“乞就本州投纳贡布,止具奏状闻奏,仍厚为官设”。[4](P.9893)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渡河之外的邛部川、两林等少数民族的朝贡记载就此消泯。与宋廷继续保持赴阙朝贡形式的西南少数民族也只剩下西南五姓蕃,哲宗朝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关系的进一步收缩成为事实。
到了徽宗朝,西南少数民族以赴阙形式的朝贡更是少见,双方之间的朝贡关系也更加淡漠,这正是因为徽宗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较前朝更为激进:“崇宁以来,开边拓土之议复炽,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洞蒙光明、乐安峒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靖州西道杨再立、辰州覃都管属等各愿纳土输贡赋。又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1](P.14182)在蔡京的怂恿下,一批诸如王祖道、庞公孙、张庄的官吏开边西南,以兴己功。王祖道招诱王江少数民族,建怀远军,后又乘南丹州莫公佞叛乱之际,收复南丹州建为观州。接着又伙同张庄深入海南黎峒,企图开辟生黎之地。[1](P.11040-P.11042)而庞公孙在西南任官二十多年,“以开边为己任”先后招诱溱、播、溪、思、费等州纳降,保霸二州蕃酋董舜咨、董彦博也被迫纳土。其“每开一城,辄褒迁,五年间,至徽猷阁待制……前后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县,多张名薄,实瘠卤不毛地,缮治转饷,为蜀人病”。[1](P.10202)虽然以蔡京为主导的各级官吏沉醉在“混中原风气之殊,当天下舆图之半”的自我功绩之中,但徽宗一朝对西南地区的开边始终是盲目的:“柄臣揽为绥抚四夷之功”,边臣“欲乘时徼富贵”,“奏贺行赏,张皇其事”。[1](P.11040-11043)但无论如何,北宋末一系列针对西南的开边举措,使得宋廷势力得以持续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造成大量拥有朝贡州额的羁縻州被置为正州,其世袭首领“出汉”成为归明人,从而丧失了朝贡的权利。因此,徽宗朝关于西南少数民族朝贡记载寥寥无几,即是继续保持朝贡关系的西南少数民族也多不再赴阙朝贡。

三、南宋时期
两宋鼎革,是宋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北宋与南宋不同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其各自迥异的政策方略。就南宋的朝贡体系而言,“南宋的朝贡体系在‘空间’和‘态度’两方面,较北宋时期大为收缩”。[9](P.115-116)受此影响,南宋时期的朝贡国家与朝贡次数也大幅度的缩减。而同作为朝贡体系成员的西南各少数民族政权,其与宋廷的朝贡关系也难以逾越这一趋势。
建炎元年(1127),保静、南渭、永顺州番人彭儒武等诣澧州献方物,“以道路未通,且令回峒”。后又于绍兴四年(1135)欲奉表入贡。[2](P.299)此外,武冈军“傜人”杨进颙、杨进京,西南大小张蕃也在绍兴年间多次请求入贡。但高宗基本上都诏令“本军婉顺说谕,路远不赴阙”,并“诏本路经略安抚司倍支回赐,依旧例发回”。[4](P.9862)绍兴十四年,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司称:“西南蕃今春起发进奉。本司契勘绍兴十一年以前诸蕃前来进奉。并依安南已得指挥,免使人到阙,只就横山寨依例管设发回今来未审合与不合发赴行在”。宋廷诏令“倍支回赐,依旧例发回”。[4](P.9862)可见,南宋初年,西南少数民族与宋廷之间的朝贡往来虽然有所恢复,但只是昙花一现。因为宋廷并未表现出过多的积极态度,反而延续了北宋中后期以来用地方输贡代替赴阙朝贡的朝贡政策。而在广西地区,其输贡点更是从宜州思立寨安排至到更加偏远的邕州横山寨。
绍兴之后,史料文献中几乎难见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朝贡记载,这是因为南宋诸帝继承了高宗时期的朝贡态度。绍兴三十二年孝宗继位,其登极赦令称:“比年以来,累有外国遣使入贡,太上皇帝盛怀冲抑,谦弗敢受,况朕凉菲,又何以堪!自今诸国有欲朝贡者,令所在州军以礼谕遣,毋得以闻。”在隆兴二年(1164)南丹州首领莫延廪请求入贡时,孝宗再次重申:“朕即位以来,敦尚俭约,例罢诸方贡献,或已至宜州界首,可令本州量与犒设,善谕遣回。” [4](P.9867)正如这两条材料所反映的一样,西南少数民族不赴阙朝贡的政策在孝宗时期已正式成为定制。而原本用来安置西南少数民族贡使的怀远驿,也在乾道二年(1166)被改造为台谏官的廨舍。[4](P.9468)
朝贡关系的持续收缩反映了南宋朝廷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日趋保守,在此影响下,南宋还重新实施“禁山”之策。“蜀之边郡文、龙、威、茂、嘉、叙、恭、涪、施、遣接连蕃夷,各于其界建立封堠,谓之禁山。” [4](P.9257) “禁山”主要是针对四川沿边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的划界措施,其目的在于隔绝“蛮汉”。“禁山”之策其实早在北宋前期就已开展。景德四年(1004),真宗下诏“戒并边居民不得擅斮木开道,与人交争”;治平初,吕大防知青城县,“特置簿抄上四至,仍卓立封堠,凿石为界,严缉官私樵采,用以限隔蕃蛮,捍蔽川蜀”。但由于西南少数民族活动区域内有着丰富的林业资源,促使汉民经常越界采伐,使“禁山”之策难以彻底施行。再加上熙、丰以来宋廷对西南地区的开拓,“蛮汉”之界逐渐模糊,而“此禁浸弛,无知之民惟利是趋,侵寻剪伐,略无忌惮”。[4](P.9514)直至淳熙七年(1180),荒废不问的“禁山”政策又被孝宗重拾,下令“禁山不得民间请佃、斫伐贩卖。仍专委县尉躬亲以时巡历,待其考满,递取邻封保明实迹,方许交替。果无违禁,量与酬赏……委通判、签判,限两月别立封堠,仍刻石(各书地名及今年所立年月)以为限隔”。淳熙九年,又对四川沿边州军小路“多裁林木,重立赏罚,断绝往来”。[4](P.9257-9258)即使到宁宗嘉泰四年(1204),还在不断重申“禁山”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实施“禁江”政策。③另外,从孝宗起开始,在西南沿边地区,为控扼西南少数民族所修筑的堡寨数量激增。如嘉定府峨眉、犍为两县,因“控带夷蛮”,所以“列置寨堡,总十有九处”。[4](P.9644)而茂州城外的岷江两岸更是对筑关寨,时任权发遣茂州杨思成言:“溪无寻丈之广,而关寨呼应相闻,乃聚五兵官于其闻”,直指堡寨修筑过甚。[4](P.9515)
这一时期,宋廷还重视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扶立。诚如上文所言,熙、丰以来,随着宋廷在西南地区的逐渐开边,大量少数民族首领献土纳降,成为归明人,旧有部落政权体系遭到破坏。而南宋伊始,宋廷就开始着手废罢西南新州,恢复原有的羁縻旧地,并重新扶立酋首。绍兴以后,扶立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范围逐渐扩大。乾道三年,“以思州地在极边,东、西、南三界接连溪峒夷人,其守把溪峒隘口,依条例许子孙承袭”。[4](P.9862)可见,原本并不属于羁縻州范围的思州在此时正式被纳归首领世袭的羁縻州。与此同时,宋廷在这一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任命,注重能力而轻视血缘:淳熙十二年七月,施州田彦武因“衰老不堪把边面”,以其子田承政承袭。[4](P.9900)嘉泰三年,针对湖南溪峒地区“蛮乱”无常,湖南安抚使赵彦励建言:“宜择素有勇智、为傜人所信服者,立为酋长,借補小官以镇抚之”。其议也得到诸司的赞许,认为“往时溪峒设首领、峒主、头角官及防遏、指挥等使,皆其长也,比年往往行贿得之,为害滋甚。今宜一新蛮夷耳目,如赵彦励之请,所谓以蛮夷治蛮夷,策之上也。” [4](P.9897-9898)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扶立,已不同于北宋时期形式意义上的册封,而是通过挑选年富力强、有威望的首领的方式,扩大西南少数民族自主权,以分担宋廷在西南地区的边防压力。在此影响下,西南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势力的整合:一些小部落被大部落所吞并,如泸南地区,以及思州、播州等地;一些靠近省地的西南少数民族则被彻底汉化,如荆湖地区溪峒部落;而极边地区,甚至诞生了较大的民族势力,如自杞、罗殿等国。这一时期成型的民族势力也大多数历经元明清三朝而不衰,其首领后裔也成为日后专政一方的西南土司。因此,有民族史学者也将南宋定义为西南土司制度的创制时期。[10]
总之,无论是严行“禁山”,还是广筑堡寨,又或是扶立首领。绍兴以降,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日趋保守的史实不容置疑。但南宋朝廷并没有照搬北宋初期以朝贡关系羁縻西南少数民族的政策,而是推陈出新,通过树立少数民族首领,扩大西南少数民族自主权的方式来施行羁縻统治。除此之外,随着南宋时期西南沿边互市贸易的逐渐发展,也使得西南少数民族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朝贡方式获取物质产品。例如广西地区就出现了针对不同贸易对象、不同贸易商品的三大博易场,极大的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民之间的物质交往。[11]南宋时期势力大涨的自杞国也正是依靠互市而兴:“汝国本一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因此可见,互市之利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惠给之甚。即使在南宋末蒙古军队压境,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自杞国还屡次向广西边臣申请,“欲坚来春市马之约”,其互市逐利的迫切之情可见一斑。[12](P.767)所以在此基础上,南宋朝廷经常通过互市的把控来钳制叛乱的西南少数民族,而不再以限制朝贡相要挟。吴儆在淳熙年间通判邕州时,告诫日益骄横的自杞国人时就称:“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买马之路”,而自杞国“乃始屈伏”。[13](P.212)又如淳熙十四年,马湖路董蛮犯境,四川安抚制置使赵汝愚要求地方政府不得放其互市,最终“还到所掳人口二十三名,锣、鼓各一面。”

四、结语
通过上文梳理,我们可知,由于宋代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在其三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数次转变,从而影响了以朝贡关系为代表的治理政策的变化。以其治理观念概貌为参考,大致可划分为北宋初期,北宋中后期,南宋时期三个阶段,而在每个阶段中也能观察出细微的异质性特点。纠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宋代根据其所处政治环境,不断调试对外政策而导致的。
北宋建立之初,在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双重威胁下,对外政策与军事部署完全倾向北方,因此针对刚刚顺服的西南少数民族,宋廷的治理观念基本上秉持着绥靖羁縻之态,希冀维持“蛮汉”两隔的态势。在采用“以夷制夷”的行政管理模式的同时,应西南少数民族所需,宋廷被动地、来而不拒地接受着西南少数民族朝贡,用最小的经济代价来换取西南少数民族的顺服,获得正统名分上的支持。但随着北方战局的稳定,原本对西南少数民族疏离的治理政策,已经难以应付中原汉民逐渐外拓,所导致“蛮汉”界域打破,“蛮汉”冲突日益激增的新形势。为此,宋廷开始有意识的主导朝贡,意图将朝贡关系作为钳制西南少数民族的手段,应时而发,使西南各少数民族从西南边境的不安定因素逐渐转变为边境的“藩屏”。伴随着这一观念的转变,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朝贡要求与限定,也不断更新完善,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层次分明、规制严谨的朝贡制度。
转至北宋中期,由于变法的开展,对外政策趋向主动,原本保守的对外政策也悄然发生变化,激进地、更具侵略性地对外政策逐渐成为主流。与之相适应的,以恢复“汉唐旧疆”为设想的远景在宋廷的南北两面逐渐展开。受此影响,原本具有隔离交趾、大理作用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此时成为宋廷南拓的障碍,因此强硬的进驻与收复取代了绥靖羁縻行性质的朝贡,大量西南少数民族受到宋廷的攻伐,或在宋廷威逼利诱下纷纷纳土称臣。而作为宋廷绥靖治理观念下的产物,朝贡关系也在这一时期暂时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哲宗一朝虽然有过“元祐更化”的政策转向,也曾一度退还开拓的“蛮地”,并重新扶植西南少数民族首领。但自绍圣之后,对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在内的对外政策又重新强硬起来,以致徽宗朝继续效仿之。
两宋鼎革之际,正是整个东亚政治局势变化的重要时段。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攻灭契丹政权后,将矛头对向大宋王朝。靖康之难后,在高宗筚路蓝缕的经营下,宋廷终于在南中国存得栖身之地,但却要时刻提防着女真人南下的威胁。在这些内外因素的交织下,宋廷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像神宗、徽宗朝那样强硬的治理模式。因此,南宋朝廷通过挑选年富力强,忠顺服帖的西南少数民族首领,重拾北宋初绥靖安边的“藩屏”之策。另一方面,由于南宋朝廷对待朝贡体系的热枕已不比北宋,在朝贡关系中,受“敦尚俭约”“重利轻名”政策倾向的影响,从原来看重政治效应转向关注经济效益。在此趋势下,处于宋代朝贡体系外沿的西南少数民族,其朝贡缩减的状况也未在南宋时期获得转机。南宋朝廷在其建立初期,就规劝那些想赴阙,重开朝贡的西南少数民族将贡物、奉表交予地方。在这之后,更是利用互市贸易逐渐取代朝贡体制。
概而论之,受制于地理环境等因素,西南少数民族在中古以前,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并未受到历代统一王朝的重视。但随着中古以来,西南少数民族在时代发展背景的牵引下,逐渐靠近历史舞台的中心区域,这引来了各个王朝的侧目,对其不同的治理政策也在摸索实践中不断展开。继唐而立的宋朝,在吸取唐朝治理西南少数民族经验教训的同时,结合其自身所处国际(主要指东亚)政治局势变化以及内部发展的需要不断调试其治理观念。作为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模式的主要表现,朝贡关系从其初创转至收缩,最后被更为丰富的治理方式所替代。这一变迁过程充分的反映了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的不断变化,也让我们看到宋代开始摆脱中古以来“重名清利”民族治理观念的桎梏,可以根据其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环境、政治需求,灵活调整西南少数民族治理方式,或者在旧有方式上挖掘出新的职能,为政权的发展运作提供了更多的现实意义。而宋代多变的治理观念,也为元明清后世王朝治理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借鉴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宋代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变迁的过程,也掺杂了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制度设想。虽然其中难免有所偏见,但在一定程度上了却满足了西南少数民族发展的真实所需,为碎片化民族部落之间的整合,以及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注释:
①参见李昌宪:《宋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尤中:《隋、唐、五代、宋王朝对西南各民族地区的经营》,《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安国楼:《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郭声波:《试论宋朝的羁縻管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刘复生:《宋代羁縻州“虚像”及其制度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4期;陈曦:《虚实之间:北宋对南江诸“蛮”的治理与文献记载》,《宋史研究论丛》2015年。
②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10859页-第10860页):“元祐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丙午,辅臣面奏:‘乞以湖北之渠阳寨复溪峒之诚州,补其旧族杨光潜之子昌达为刺史,先奏知,续入状,画一行之。’”
③参《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515页)方域一二记载,有臣下奏言:“窃缘禁山之下,即是皁江,可以直至成都,其势甚顺,获利为多。是致官司指为出产所在,公私并缘肆行采斮,夏秋涨水之际,结为薭伐,蔽江而下,经过津岸,殆无虚月。向之茂密,今已呈露;向之险阻,今可通行……臣窃思之,山以禁名二终莫能禁者,一江实为之累也。若于上流特置联锁以杜绝津载,则弥亘连袲之母,不容顺流而下,故禁江尤切于禁山”。
参考文献:
[1] (元)脱脱等.宋史 [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清)徐松编.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 (宋)王应麟.玉海[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7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
[6](宋)沈括.梦溪笔谈 [M].北京:中华书局,2015.
[7](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 [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8] (宋)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0]史金波.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刍议[J].中国史研究,2017(1).
[11]朱文慧,王元林.宋代广南西路的三大博易场和海南岛的对外贸易[J].海南大学学报,2010(1).
[12]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9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
[13] (宋)吴儆.竹洲集[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Z].台北:商务印书馆,2008.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
作者:林建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